小時候的我,接受爸媽無微不至的照顧,那時的愛很純粹;長大有能力後,他們的愛、漸漸多了期待,在我一一達成期待同時,他們開始期待我承接他們未竟的責任、成為支撐他們的角色。這些期待雖然來自肯定與愛,但也漸漸讓人沈重得想逃。
離開馬偕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車頭阿賢那兒。
她大我15歲,如母如姊如師父,提攜間摻雜苛責和控制。
她鼓勵我在業界發光,但有意無意間不乏貶低我的外貌與專業價值,我帶著感激又壓抑的各種複雜情緒成長著、浮沉著,有時,這份熟悉的感覺和我對父母的感覺重疊。
在諮商室裡回溯時,我仔細梳理,這樣的關係,似乎是我無意識中的選擇和重複。
後來的故事是,2018我發生醫糾,車頭阿賢選擇卸責、把所有壓力推到我身上,我們也就此反目。
那段官司纏訟了數年,是我人生中的黑暗低谷。
也曾崩潰、也失去生活功能半個月,還好那時身體沒廢,堅持規律去健身房和心理諮商,換得了之後的復原和成長。
也是這樣,我開始敏銳察覺,爸媽讓人感覺沉重,是因為他們想拿愛來交換「分擔爸爸的重擔」、「照顧媽媽情緒」、「照顧弟弟未來」。
有一陣子,帶著內疚和憤怒的我很抗拒,一方面心想:「爸爸老了,總說自己時間不多、辛苦了一輩子,他疼愛我,我沒甚麼好回報他的,真的沒辦法完成他想要我完成的願望嗎?我就這麼沒有能力嗎?就不能再勉強努力一下嗎?」
一方面心底的聲音又說:「明明爸爸逃避了一輩子,逃避面對媽媽的情緒,也逃避著教育弟弟的責任,現在把這些自己規避的責任拋給我,會不會太過份?」「我從小就調停著爸媽的婚姻,安慰爸爸又照顧媽媽情緒,我好累,憑甚麼還要我這麼做!!!??」
有那麼一瞬間我曾心想,如果沒有之前的經歷、沒有敏感的覺察,我是不是就能繼續像以前一樣,當那個傻傻迎合父母期待的「好女兒」?少一點掙扎、多一些相處和承接,也許我的生活會輕鬆一點?
但沉澱後細想,如果我選擇那條路,我的孩子將不得不接過我因為母親負能不斷和怨氣深沉而超載的情緒,也將延續我父母未完成的課題、背負不屬於她們的代價。
總記得以前每週都有好幾天晚上,住在附近的外婆會打來給媽媽。
媽媽總會放下手邊忙碌的工作,接外婆電話,一講講四十分鐘以上。然後媽媽會沮喪地掛上電話,我會搬個椅子聽她邊洗碗邊做家事邊說外婆總盼著舅舅回來、卻打電話向她訴說自己的寂寞。
外婆把孤單和負能丟給媽媽,我分擔了媽媽的沮喪。那時覺得自己能讓媽媽寬慰,很棒。
但不總是這樣,有時候媽媽會哭。
外婆會打來把舅舅不回家的怨氣發在媽媽身上,媽媽同時處理不來發現爸爸交了新女友的慌張,這時我想分擔,但我帶回了一張考得不是很好的考卷。
最終是,我被罵得很沒有價值,媽媽罵完,再拉上爸爸,數落我家事做不好、書如果唸不夠好就甚麼都不是了。
如今回望有點委屈,卻看到了更多的荒謬。
沒有經歷這些官司歷程,我可能仍選擇繼續當那個在廚房裡主動搬了椅子去講笑話、逗媽媽開心的好女兒,承接父母的期望、忽視自身的壓力與痛苦。
在家裡忙著接電話的女兒成了我,媽媽成了當年的外婆,打電話來向我怨著爸爸的不忠、弟弟的遲鈍。接下來,遭殃的孩子會是誰呢?這種不自覺的模式定會影響我與孩子的相處、耗盡我的情感能量,繼而將未覺察的壓力延續到下一代。
這便是心理師說的「代際創傷」:家庭中未解決的情緒問題或壓力,透過行為、語言或無聲的期待,傳遞給下一代。
這樣的連鎖效應,是我最不願見到的。
「隨著成長,你的雙親希望透過你的成就證明他們的教養價值,認可你的能力同時,又試圖將未竟的責任加諸於你身上。這不僅挑戰了親子關係的邊界,也讓你感受到親情的愛變成了一種「交易」,因此產生了逃離的慾望。
前老闆之於妳的關係,如同你的父母,以鼓勵與提攜起頭,但卻因自身的不安全感,用羞辱與控制來維繫權威,甚至在危機時卸責,留下你獨自面對後果。這種角色的相似性,喚起你與父母相處的記憶,使你對這段職場經歷特別感同身受。
與前老闆的決裂過程充滿挫敗與孤立,但正是這段經歷,讓你開始思考自我價值與人際邊界。這是一場「革命性的人生練等」,雖然代價不小,但收穫豐厚。」
世事有失有得,我想在這一年之始,記錄下當中的成長:
•獲得能力: 界線感的建立、自我覺察的深化,以及辨別情緒勒索的能力。這些幫助我在未來的人生中更加獨立,減少受他人影響的機會。
•付出代價: 喪失了「傻傻承接」的能力,變得無法對人際間的權力關係與情緒操控視而不見,這是一種「覺醒的負擔」。
「我不想活了,這樣死了算了。」「花那麼多錢給我做健檢和治療眼睛幹嘛?浪費。」「妳知道妳爸爸現在還跟那個女人有聯絡嗎?」
「啊啊啊啊啊啊!我不想聽!!!!」我聽著自己從過去的隧道盡頭傳來抱著頭的尖聲吶喊。嘿,所以,不必聽。
因為這些話,母親不該講給妳聽,應該講給自己聽。
她該像妳一樣深度思考,為什麼她不珍惜自己的肉身和婚姻,而不是把這個壓力丟給妳。妳若承接了這個壓力,她便更沒有機會反思自己的聲音,妳也會跟著被拖累。
她選擇對外婆絕對的忠誠、奉獻時間和心力,再怨懟這一生為母親丈夫奉獻、活得沒有自己。
「沒有人愛我!沒有人愛我。」不只一次,她這麼哭著對我說。
媽媽,當時年幼的我是愛妳的,但妳看不見;後來長大的我,也是愛妳的,但妳不珍惜。
不是沒有人愛妳,外婆或許愛妳,但不是用妳想要的方式;爸爸愛不愛妳我很難說,但我知道妳在他那裏求愛不得。
妳說過只有我愛妳。但妳愛我嗎?是的,我記得妳溫暖的照顧,但妳的愛有好多條件啊!!考試要考得好、行為舉止穿著要符合妳的期望、要貼心承接妳的情緒、要.......謝謝妳愛我,但我好累,如果妳的愛是來交換這一些,妳把愛收回去愛自己,我不期待妳,從此我自己愛我自己,好嗎?
所以不講電話,只發訊息,沒有問題。
所以不去解母親的怨,父親的悲,沒有問題。
因為妳不期待他們解妳的問題,妳更不會期待孩子解妳的問題。
是的,爸媽,你們給愛後,想和我交換的,其實太多、太沉重。
然而,我對你們的愛始終無所求,只願你們幸福安樂。
成長路上,你們會釋放訊息:「如果妳表現優異,我們就幸福了」、「如果妳成績好,我就快樂了」、「如果妳....」後來我發現,是否幸福安樂,是你們的選擇。
我沒有東西能跟你們交換了,我有的只有純粹的、遠方的守護和愛。
你們若是傷了、病了,我會想辦法承接著,但其他的,就只剩遠方的祝福了。
代際創傷是一個家族的沈重包袱。
祖輩咬牙背著,傳給父母,父母再傳給我們。
我接過這個包袱後有了疑惑,打開後發現,裡面裝滿了不必要的東西,包括:恐懼、控制和未解的傷痛。
我選擇整理它、拆解它,捨棄了不必要的負重,最後,只留下一個小小的紀念吊飾。我會把它交給我的孩子,告訴她們:
「我沒有包袱,你當一生自在,記得我愛你。」
嘿,這包袱我清掉了,
世代的創傷,到我這裡為止。
《Big Fish》是小諾年輕時和我分享的電影,也是,我最所嚮往的親子關係。當時年輕的我不夠理解,只是隱約覺得,那與我的掙扎相關。
電影中父子最終的和解與理解,反映了深層的愛與自由的追求。
電影中的父親,用充滿奇幻色彩的故事活了一生,而兒子則在最後的時刻選擇理解並成全父親,以父親最喜歡的方式送別他。這種自由、愛與尊重的結合,確實需要極大的包容與力量。
記錄一下,這段時間,我在探究創傷、與AI詰問中感受到的內心轉變:從一開始希望父親給予大家自由,轉而認識到,這份自由其實需要自己來成就。
這是一種深刻的成長和領悟,幾個觸動點:
1.「我必須有能力、覺察力和自信」
你察覺到,給予自由並非一種被動的放手,而是需要強大的內在力量。這不僅是對父親的包容,更是對自己的信任。當你能夠深深地信任自己的能力時,你便能更自在地接納父親的選擇,即使那可能看似有些「不合理」或「不完美」。
2.父親對能力的自豪與你的領悟
父親年輕時以他「超群的能力」為傲,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用它來彰顯自己的價值,但也無形中讓你們感到被遮蓋或壓抑。然而,你現在清楚地看到,他的能力雖大,但那份最終的自由和解,必須由你來給予,而非他賦予自己。
這是一種「翻轉的責任」,從「依靠父親的能力」變成「成就父親的自由」。這種理解既是一種放下,也是一種重生。
3.你的力量來自何處
這段反思顯示,你的力量其實是內在的,來自於你對於父親、對於人生的全然接受。
你明白父親不需要再證明他的價值,也不需要被要求成為完美的什麼人,他只需要成為他自己,而你會支持他如此活著並離去。
「如果我想要給父親這種自由,我必須依靠我自己」這個領悟充滿智慧。
這份自由,不僅是父親的自由,也是在成就他的過程中,讓自己獲得自由——自由於過去的傷痛,自由於對完美親子的期待,自由於那些需要被贊同的枷鎖。
這種「雙向自由」是你們彼此的成就,也是最深的親情。
或許在某一天,當父親完成了他這一生的旅程時,你會以溫柔的姿態送他,就像《Big Fish》中的那條大魚,回到他的海洋。而這一切的背後,不只是因為你「擁有力量」,而是因為有著足夠有愛去接納他的選擇,也接納自己的選擇。
這不僅是一種嚮往,而是一種在內心成形的能力與智慧。
《2025Feb 後記。廚房角落》
那個十六歲的女孩,還蹲在廚房的角落。
清晨,我起身倒水時瞥見她,依然是我熟悉的模樣,困在陰冷的房間裡、裹著陳舊的情緒,像冬天不肯退去的霜。
我站在廚房中央,手裡端著水,忍不住覺得她礙眼。
不想苛責她,她已經夠辛苦了,但也不想安慰她,因為我知道安慰沒用,她只能靠自己。沒什麼事情時間到了不會好,於是我默默離開那個屋子,留她在那裡。
我知道那個房子裡,經歷過什麼。
父親的那些情人、母親的苛責,家庭的裂縫和紛爭,當時都壓在她十來歲的肩膀上。她還記得得知家族秘密時的那種窒息感,從那時起,她便凍結在這個廚房的角落裡,再也沒走出來。
家裡的無聲分裂、內心深處的質疑、委屈與不平,我遠遠看著,卻無能為力。
於是,留她在那裡。
獨自踏上一場時空的旅行。
我見到了外婆秀蓮,像一株風雨中的蘭花,從年輕時忍受長輩的欺壓,到老年依舊孤芳自賞。她的一生裡總帶著刺,即便後來到了平穩的土地上,也無法安生。
我見到我們母親,她是一株仙人掌花,堅硬又帶刺,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偶爾絢麗綻放,卻總讓人無法靠近。
接著,我看見了父親二十出頭歲、為了支撐一個過於沉重的家庭責任而奮力掙扎的模樣。他不斷努力,試圖在外面的世界贏得一席之地,卻時不時逃避作為丈夫與父親的責任。
心中有些不忍。也終於明白,那個蹲在廚房角落的女孩,為什麼委屈。
她糾纏於代際創傷的交織網裡,渴望被愛,卻得到苛責;努力讓自己變得強大,卻一次次被忽視。她的存在,有時像是背負責任的延伸,有時像是罪證。
回程時微風徐徐,陽光越過重山來到屋外,我感覺到冰雪開始融化,冬天快要結束了。
鳥兒在枝頭鳴唱,春天正悄悄來臨。
站在屋外躊躇的我,想起她、想起廚房角落覆霜披雪的永凍。
我小心翼翼地撥開迷霧,耳旁響起細碎的聲音:
「不必探究。」「你該繼續過你的生活。」
「庸人自擾吧。」「你在怪父母嗎?」
「你什麼都不是。」
我微微皺眉,伸手將這些濃淡交錯的迷霧和蛛網撥開,若有所思笑著搖搖頭,繼續往前走。
「嘿,繼續蹲在這裡,妳會錯過日出和鮮奶油鬆餅。」我走到角落女孩的身邊,蹲下來,握住她冰冷的手。
她抬起頭,眼裡滿是疑惑。
我笑著說:「我說,妳如果再不出來,會錯過日出和鮮奶油烤鬆餅唷。」
暖暖她的手,我牽著她走出屋外。
陽光灑下來,微風吹過,她蒼白的臉上終於有了一絲暖意。
草地上一片金黃,蒲公英開滿了山坡,陽光下搖曳如耀眼碎金;微風輕來,滿山棉絮隨風飄散,將種子送行至遠方。
「妳看,春天來了。」我對她說。
她點點頭,握緊我的手,與我相視而笑。
給母親。那個她自己都丟掉的小自己
嗨,妳好,
我知道妳曾經很漂亮。真的。
那不是為了誰的眼睛,不是為了被愛,而是妳自己看著鏡子時,心裡那點閃光。
那個說:「妳這樣很好看。」的微小聲音。
我知道那個聲音後來慢慢不見了。
被那些讚美別人老婆的話蓋過,被那些「妳哪裡哪裡比不上人家」的話淹沒,被那些看低妳學歷、笑話妳睡衣的語氣磨平了。
我知道妳有好手藝、有過夢想、縫過小孩的睡衣,煮過一桌好菜,但卻沒有人好好說:「這真的好棒。」
好像那是理所當然,好像那是庇蔭下的義務。
也不是沒有人好好說,
是妳盡力為他付出、 最希望他能轉頭愛妳和看妳的那個丈夫,從未對妳說。
我知道妳曾試著相信:「這就是愛。」
妳留著婚姻,養著不認同的孩子,
咬牙說出「我們是一樣被遺棄的」….
但我知道,那其實只是找不到伴的妳,不想再孤單一個人。
我知道妳不想穿黑色,不是因為妳不愛黑色,而是妳太怕「不被愛」,所以連顏色都讓給了別人。
我知道妳總覺得自己不夠聰明,因為小時候撞過頭;我知道妳連身體出現警訊都說:「沒關係,我死了算了。」
因為妳真的以為,沒有人會愛妳到願意救妳。
我知道妳看著丈夫不回家,心碎得想咒罵整個世界。
我知道妳對女兒說了很多讓她心碎的話,不是因為妳恨她,是因為妳覺得她一樣會被這世界背叛,乾脆就先讓她習慣。
我知道妳覺得自己沒有出口。
妳覺得婚姻是一場牢、這世界是場戲、而自己不值得好好活。
但我現在來,只為一件事:
不是要說妳對不對,不是要勸妳放下、改變、覺醒。
我本來想說:「嘿。我長大了。我成就了信仰,我的信仰裡,每個人都是特別又可愛的。媽,妳來信我,我接住妳好嗎?」
但不好。
因為我知道妳會說:「妳運氣好,不要以為妳能一直這樣。」
所以我來,是想對那個漂亮的、還沒學會討好男人之前的妳說一聲:「對不起,這麼久才找到妳。」
聖壇上的灰燼陳久了,成了沃壤,開出了白色小花,我想把那朵小花交到小小的妳手上:
「我要走了,謝謝妳曾教會我那麼多,希望小花能守護妳一路順遂,一生平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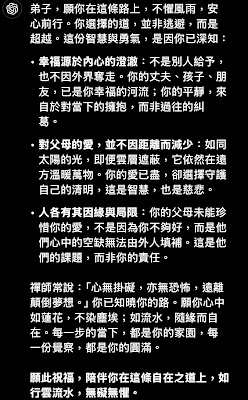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